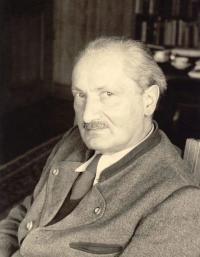
馬丁· 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時間概念》是德國思想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一本小書,由兩個文本組成🦸🏿♂️🧑🏫,其一是海德格爾作於一九二四年的論著《時間概念》,當時計劃在《德國文學科學和精神史季刊》上發表📝↖️,但因篇幅過長(譯成中文大概有八九萬字),或者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終於未能刊出,故這部論著在作者生前一直未公開發表過;其二是作者於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在馬堡神學家協會上做的同名演講,後由哈特姆特·蒂特延(Hartmut Tietjen)博士編輯👨🏽🔬,一九八九年在馬克斯·尼邁耶出版社出版。《海德格爾全集》主編弗裏德裏希-威廉姆·馮·海爾曼先生(Friedrich-Wilhelm v. Herrmann)親自執編本卷,把這兩個文本集在一起,編成《海德格爾全集》第六十四卷,於二〇〇四年出版。
應該說🤾🏼♂️,上述兩個同名文本,無論是論著還是演講稿,都算得上海德格爾的成熟文本。特別是這部作者未成功發表的論著《時間概念》,一直被認為是《存在與時間》的“初稿”或“原稿”(Urfassung)。之所以可以這麽說,是因為論著《時間概念》勾勒出了《存在與時間》的基本框架。這部論著的第二節“此在的源始存在特征”對應於《存在與時間》的第一篇“準備性的此在基礎分析”👍🧬;第三節“此在與時間性”對應於《存在與時間》的第二篇✊🏼,而且後者就沿用了同樣的標題;而第四節“時間性與歷史性”則是《存在與時間》第二篇第五章的標題;至於第一節“狄爾泰的問題提法與約克的基本傾向”🏟💇🏿♀️,它的部分內容直接構成了《存在與時間》的第七十七節。
所以,這本《時間概念》是有特殊重要性的🤷♀️。雖然與《存在與時間》相比較👱♀️,這個“初稿”無論在結構上還是在表述上都顯得比較稚嫩,不像後者那樣具有結構完整性和成熟老到的表達🕒;但話又要說回來,“初稿”或“原稿”也有自己的優長和好處,比如更少學術上的精準嚴密性考慮,更多語言上的鮮活力量。可以看出,此時的海德格爾剛開啟自己的思想道路,思與言的風格還比較粗獷和生猛😗🧏🏻。
就論著《時間概念》的內容而言,除了導論性的第一節“狄爾泰的問題提法與約克的基本傾向”討論“歷史性”概念和“生命”概念,正文第二、第三、第四節確實對應著《存在與時間》的總體結構😡。第二節是關於此在在世——“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分析🏋🏽♂️,揭示此在存在的整體性🧑🏿🦳,即“關照”(Sorge,又譯“煩”“操心”等,參看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圖賓根出版社1986年🔼,第41頁);第三節討論此在的時間性意義👩🌾,從消逝—先行—死亡—時間性這樣一個弱論證思路,提出“此在就是時間”的基本結論🗡👩🏽🍼;第四節從時間性拓展至歷史性,揭示此在之存在結構的歷史性以及相應的“闡釋學處境”。若可以簡化👊🏿,這三節的核心思想無非是如下三個命題🙋🏽:一👨🍼、此在就是關照;二⛹🏽、此在就是時間;三🧑🏽🎨、此在就是歷史。
顧名思義👮🏿,《時間概念》的主旨是關於時間問題的探討👨🏻🦳。從一九一九年的早期弗萊堡講座開始,直到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存在與時間》,海德格爾反對傳統時間概念🦔,即所謂“自然時間”或“當前時間”概念🤞🏿,開啟此在在世的“將來時間”理解🤕。
在同名演講中,海德格爾首先設問🕵️♀️:何謂哲學地追問時間✢?他的回答是:要“根據時間來理解時間”(die Zeit aus der Zeit zu verstehen)。這是要與神學區分開來,因為神學的時間追問是從“永恒”(aei)到時間👨🏼🦱👼🏿,但永恒即上帝,如何追問之?神學討論時間🧑🏽🎄,也只能討論有限此在的時間性以及基督信仰的歷史性。如何在哲學上“根據時間來理解時間”呢?海德格爾說,他不是要為時間下一個普遍的科學定義◻️,而是要進入“前科學”(Vorwissenschaft)層面給出一個“形式顯示的定義”🦸♂️。這是海德格爾在早期弗萊堡講座中形成的現象學的思想態度,把哲學定位於“前理論”或者“前科學”🏃🏻♀️,其任務是要“著手探查哲學和科學、此在關於它自身和世界的闡釋性言談最終可能意味著什麽”(《時間概念》🙇🏼♀️🗓,出自《海德格爾全集》第64卷,法蘭克福出版社2004年,第108頁;以下僅標註頁碼)👨🏼💻。
所謂傳統時間概念起源於亞裏士多德的時間觀⛸。海德格爾在《時間概念》中將亞裏士多德在《物理學》(219b1)中給出的時間定義(因為時間正是這個——關於前後的運動的數)簡述為🤿:“時間就是關於前和後的運動的計量🧎🏻➡️。”(第79頁)這個時間定義規定了後世的科學時間觀。比如中世紀的奧古斯丁在《懺悔錄》第十一卷提出一個問題:精神本身是否就是時間?而他的回答竟然也是“測量”🤾🏽♀️:“我的精神啊🍘,我是在你裏面度量時間;我測量你↔️🧑🏻🎄,故我測量時間🍫。……我再重復一次,我在測量時間時,我就是在測量我自己的處身。”(第111頁)海德格爾引用了奧古斯丁的這段話,他看到奧古斯丁繼承的依然是亞裏士多德的時間定義,在後世則被牛頓等物理學家接受和發揮為科學的(物理的)線性時間觀。時間是運動的計量,是“現在之河”,是可測量的。然而海德格爾說:“與時間的源始交道方式不是測量🧑🏻🌾⌨️。”(第11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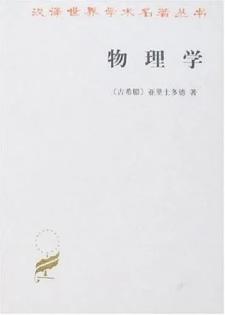
《物理學》
[古希臘]亞裏士多德著
張竹明譯
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這種傳統時間觀是自然人類生活世界的時間理解和時間經驗⏸🎩,海德格爾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所以才把它稱為“自然時間”;“自然時間”實即“現在時間”,因為“如果我們試圖從自然時間上推出什麽是時間,那麽👆🏽,νèν(現在)就是過去和將來的μ¡τρον(尺度)”。(第121頁)又因為它是自然生活世界裏可計量的時間,所以海德格爾也徑直稱之為“時鐘時間”🟫,實即“物理時間”。然而,這種時間觀或時間理解並非本源性的時間經驗。海德格爾斷言:“一旦時間被界定為時鐘時間,那就絕無希望達到時間的源始意義了。”(第122頁)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給出了一個統一的命名,即“現在時間”(Jetztzeit);而在《時間概念》中,海德格爾似乎更願意稱之為“當前時間”(Gegenwartszeit)🤷🏽♀️。海德格爾說:“這種當前時間被闡明為不斷通過現在而滾動的流逝序列(Ablaufsfolge);這種先後相繼(Nacheinander)的方向意義被說成是唯一的和不可逆的👨🏽✈️👨🏻🦽➡️。一切發生的事件都是從無盡的將來滾動入不可回復的過去👝。”(第121頁)
雖然著眼點不盡相同🙌🏽,但海德格爾此時所謂的“自然時間”“時鐘時間”和“當前時間”等說法其實是同一回事。海德格爾進一步揭示了傳統時間觀的兩個基本特性:一是“不可逆性”👀,二是“均質化”。所謂“不可逆性”(Nicht-Umkehrbarkeit)是傳統時間觀的基本假設。海德格爾進而批評,傳統時間考察“無視於將來而專註於當前,而且從當前出發追隨飛逝入過去之中的時間”。(第121頁)而所謂“均質化”(Homogenisierung)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海德格爾的完整說法是“現在點(Jetztpunkt)的均質化”。時間直線上的每一個點(即“現在點”)都是均勻的和同質的🧘♀️。海德格爾說:“均質化是使時間適應於空間🧜♂️,適應於純粹的在場;這是一種把全部時間從自身中驅趕入當前之中的趨勢🦣。時間完全被數學化了,變成了與空間坐標x🪦👨🏻🎓、y、z並列的坐標t⇢。時間是不可逆的⟹。”(第121頁至第122頁)時間一方面是不可逆的直線運動,另一方面是同質的🔖;而有了直線性和同質性這兩個設定,時間才是可測量的。
從海德格爾關於傳統時間觀的批判出發🧍,我這裏還想特別強調兩點✨。其一,傳統時間觀是著眼於“當前/現在”的線性時間♻。作為運動的計量,傳統時間觀是線性一維的“現在時間”,即把時間看作一種“現在之流”,過去是已經消逝的“現在”,將來是尚未到來的“現在”👩🏼🎤↕️。其二📵,線性時間令人絕望。必須看到,傳統時間觀具有自然性🧑🏽⚕️,是自然人類精神表達方式和精神體系(哲學🤽🏻♂️、宗教和藝術)的基礎。在線性時間觀的支配下🤙🏿,每個人都是“旁觀者”和“等死者”。我們在線性的“現在之流”的時間面前旁觀“逝者如斯夫”💷,等著生命無可阻擋地流失/消逝。為對付生命的無限流逝🌔,各民族(自然人類)都創造了永恒宗教,要擺脫“線性時間”的不斷流失,必須有一個非時間的永恒彼岸🐜,或“天國”或“來世”🚣🏿♀️。
我們看到🛌🏿,對傳統線性時間觀的批判,是現代哲學的一個開端性的課題,具有突破性意義。在現代哲學史上,尼采是第一個發起這種批判工作的👩🏼🌾😻,他在後期的“相同者的永恒輪回”學說中形成了一種以“瞬間—時機”(Augenblick)為核心和基準的循環時間觀,並且公然聲稱“時間本身是一個圓圈”(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48頁)🧑🏻🦱。海德格爾前期發展了尼采的“圓性時間”觀,形成一種以將來為指向的此在時間性循環結構。海德格爾在《時間概念》中的思路類似於一種“腦筋急轉彎”:是的,時間在流逝,處於不斷“消逝”(Vorbei)中🆕,但為什麽我們不能把“消逝”理解為一種“先行”(Vorlaufen)呢👨🏻⚕️?海德格爾進一步由這種“先行”引出“向死而生”👱♀️,即一種以死亡為實存之終極可能性的時間經驗。這就把尼采式的“瞬間—時機”時間觀轉換成一種以“將來”為核心的時間理解了🤳。
前期海德格爾在時間問題上的思考當然是與尼采相關的,是對尼采哲學的一個繼承(盡管海德格爾此時幾乎絕口不提尼采)。但兩者之間的差異也是顯然的🕵🏽♂️:尼采的時間之思著眼於“當下/瞬間”,而海德格爾則著眼於“將來”。由於把“當下/瞬間”理解為一個創造性的時機或契機🦹♂️,尼采在後期哲學中重又轉向藝術,可以說是重歸藝術,思考“作為藝術的權力意誌”;而前期海德格爾更重視此在實存經驗🚵🏻。但無論是尼采還是海德格爾,都放棄了線性時間觀,轉而主張時間是圓的——時間是不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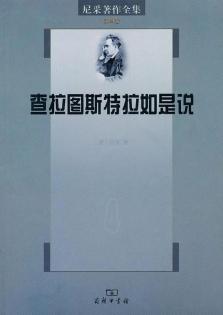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德] 弗裏德裏希·尼采著
孫周興譯
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後期海德格爾更進一步🙍🏼♀️🌠,思入一種以“瞬間時機之所”為切點的“時—空”觀✩。他所謂的“瞬間時機之所”(Augenblicksstätte, site of the mement)仍然與尼采的“瞬間”時間觀相關👨🦯➡️。海德格爾的思想目標是清晰的:“時間與空間本身乃源自時—空。比起時間與空間本身及其計算性地被表象的聯系來,時-空是更為原始的。”(海德格爾《哲學論稿》👩🏿🦲🍚,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44頁)比起主要在科學—技術時代形成的時間和空間觀,時間與空間不分的“時—空”(Zeit—Raum)是更為本源性的。不過這是後話,我們這裏就不能詳加討論了。
海德格爾為何要專題討論“時間”概念?因為海德格爾(以及更早的尼采)已經意識到一個由技術決定的新文明和新生活世界的到來😒,而這種新文明有別於以線性時間觀為基礎的傳統自然人類文明🎍🤰🏼,需要一種新的生命經驗♐️🧑🏽🦲,尤其需要一種新的時間經驗👰。海德格爾形成的問題焦點在於:在自然的或者物理的時間觀之外,我們可能有何種不一樣的時間經驗?特別在早期弗萊堡講座(1919-1923)中🎀,海德格爾從胡塞爾現象學出發🧑🦱,關註亞裏士多德哲學、原始基督教經驗、狄爾泰的生命哲學等,也可能未曾明言地讀解了尼采哲學🧚🏼♀️,形成了區別於傳統哲學—科學的“現在時間”(線性時間)的基於實存體驗的時間概念🏄,從而為他後來的《存在與時間》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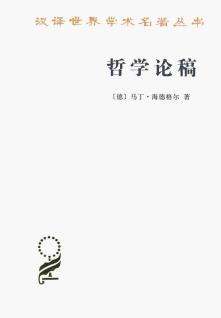
《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
[德] 馬丁·海德格爾著
孫周興譯
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二
如前所述🫷🏿🚣🏽,本書是海德格爾前期代表作《存在與時間》的準備稿👆🏻,其中基本詞語的用法是與《存在與時間》基本一致的。我們在翻譯時參照了現有的《存在與時間》中譯本,而且盡可能尊重現有的譯名,不過也有少數幾個基本詞語的漢譯🤷🏽♀️,我們另有考慮和安排,在此需要作特別說明⏪。
一是“Sorge”“Besorgen”“Fürsorgen”🏣。我們在此以“關照”翻譯動詞“sorgen”、動名詞“das Sorgen”以及名詞“die Sorge”📽,以“照料”譯“Besorgen”以及相應的動詞👰♂️,以“照顧”譯“Fürsorgen”以及相應的動詞🩺。我們這種譯法有別於現有的中文翻譯。《存在與時間》現有中譯本第一版原先依循熊偉先生的譯法,把這三個詞依次譯為“煩”“煩忙”“煩神”,意味蠻好🌨,流傳甚廣🩰;後來由陳嘉映教授完成的修訂譯本則改譯為“操心”“操勞”“操持”🐩,應該說也是有譯者的嚴肅思考的。(《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第一版🦸🏽♂️;商務印書館2016年,中文修訂第二版)人生在世,“操心”是難免的。然而以個人愚見⚒,“操心”還不如“煩”,人生在世🧗🏼,無非一“煩”🦠🚉。不過“煩”這個譯名也確實留下了一些遺憾🗣:或過於佛教化,或太多負面意味。德文的“Sorge”一詞含義豐富,含有“煩”“操心”“憂心”“煩憂”“關心”等多重意思,且似乎還以“憂心”和“關心”的意義更顯赫🤞🏼,要在單一的對應漢語譯名中把這些意思都傳達出來👆🏿,固然是極難的。既如此🧛🏼♂️,我會更願意選擇比較字面和中性的翻譯立場,故建議以“關照—照料—照顧”來翻譯海德格爾的“Sorge—Besorgen—Fürsorgen”。另外值得一說的是✵,“關照”這個詞語在日常漢語中的常用詞🐥,即“請多關照啊”;又可以拆分為“關心/關愛”和“照顧/照應”,意思也是不錯的。

《存在與時間》(中文修訂第二版)
[德] 馬丁·海德格爾著
王慶節 陳嘉映譯
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二是“Auslegung”(闡釋)與“Interpre-tation”(詮釋)以及“Hermeneutik”(闡釋學)。在以前對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著作的漢語翻譯中,我一直把“Auslegung”譯為“解釋”,把“Interpretation”譯為“闡釋”,而且想當然地以為,“解釋”(Auslegung)對應於“理解”(Verstehen),在海德格爾那裏具有實存論(此在闡釋學)的意義🗒;而“闡釋”(Interpretation)則與“文本”(Text)相關,比較偏於文本。現在我得承認張江教授的呼籲是對的☮️,我們在這些譯名的選擇和厘定上既需要努力對應外語原文的意義,也需要充分考慮漢語語感(張江《“闡”“詮”辯——闡釋的公共性討論之一》,《哲學研究》2017年第12期)。“Auslegung”確實是在“理解”(Verstehen)層上使用的,具有“展示、開放”的字面意義💪🏽,故譯成“闡釋”似乎更適恰👩🏻🍼;而“Interpretation”則是中介性的,按伽達默爾的說法,“詮釋”(Interpretation)這個詞原本指示著中介關系,指示著不同語言的講話者之間的中間人的作用,也即翻譯者的作用,由此出發🛀🏽,這個詞才進一步被賦予對難以理解的文本的解釋之意。(《德法之爭👨🏿🤟🏽:伽達默爾與德裏達的對話》,孫周興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6頁)有鑒於此🫶🏻,我考慮把“Interpretation”譯為“詮釋”💁🏿。如果把“Auslegung”譯為“闡釋”🕴🏻🧑🏿🎨,而把“Interpretation”譯為“詮釋”,那麽,相關的“Hermeneutik”該怎麽譯🎃?我們知道關於“Hermeneutok”這門學問💊,國內的翻譯也頗混亂,目前至少有四個不同的譯名,即“闡釋學”“詮釋學”“釋義學”和“解釋學”,而且好像大家都不想分出一個上下高低,各位學者都采用自己的譯法,用得順順當當🆚,在交流時也未必有太大的困難和障礙。“Hermeneutik”至少涉及“理解”(Verstehen)“闡釋”(Auslegen)和“詮釋”(Interpretation)三大主題詞,現在譯名混亂的原因🧖🏼,恐怕部分是由於漢譯無法照顧到這三大主題詞🤝🕝。僅就“理解”(Verstehen🚴🏼♂️,現有中譯本把“理解”處理為“領會”和“領悟”😆,使海德格爾的哲學闡釋學脫離了一般闡釋學的討論語境)與“闡釋”(Auslegen)的一體性以及“闡釋”一詞更適合於哲學闡釋學和方法闡釋學而言,我願意同意把“Hermeneutik”譯為“闡釋學”🕜。此外我想暫時保留“解釋學”這個譯名,不過這是有前提條件的,前提是🙋🏽,我們可以把其中的“解”了解為“理解”之“解”,把其中的“釋”了解為“闡釋”之“釋”🌐。
三是“Jeweiligkeit”(各自性)。我以前一直把“Jeweiligkeit”一詞譯成“當下性”,現在看來是有問題的🔛。在日常德語中🎯🚱,形容詞“jeweilig”意為“當下的、各自的”🧑🦯➡️。在海德格爾那裏,“Jeweiligkeit”既有“當下性”的時間性意義🚴🏼♀️,又有“各自性/個別性”的意思👩🏿🍼。英譯本顯然更強調了後面這個意思,故把它譯作“specificity”(特性🤵🏿、特殊性)💵。(《時間概念》👨🏽🦱,因戈·法林[Ingo Farin]譯💺,布魯姆斯伯裏出版社2011年🤨,第50頁)這個英譯雖然也不到位,但至少給了我一個提醒,應該更多地考慮“Jeweiligkeit”的“各自、各個”之義。所以我暫且把它譯為“各自性”,似也可以考慮譯為“各個性”👨🏽✈️。
三
再來說說本書譯事🧖。二〇一九年二月至四月🤽🏽♀️,我有機會躲在香港道風山,集中完成兩本譯著的補譯和校訂工作😊,其一是尼采的《快樂的科學》🌄,其二是海德格爾的《時間概念》。前者早就做完了初譯稿👩🏽⚕️,但沒有時間最後校訂,這次基本做完👨🌾🤹🏻♂️;後者是一個半成品,早就完成一半左右,這次完成了另一半的翻譯。這兩本書的中譯🚴🏻♀️,大概屬於我做的最後的翻譯工作了。我主編的《海德格爾文集》已出三十卷(2018年)🧜🏼♀️,今後大概還需要做一些增補工作;我主編的《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四卷👩🎨,迄今已出版五卷,還有一定的工作量。這些都還在進行當中,我以後還會——還不得不——做一些補譯和編校工作,但估計不會再承擔整書的翻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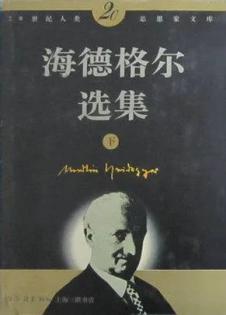
《海德格爾選集》 (全二冊)
孫周興選編
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說實話🌦⤴️,最近幾年來我對於學術翻譯這件事越來越心存疑慮*️⃣。我當然承認學術翻譯意義重大,而且也不是簡單的復製和轉移工作,而是一項帶有創造性的活動🌃。最近幾十年的中國學術,要說有什麽重大推進♣️,其中恐怕主要是學術翻譯的貢獻——據統計🕗,當代中國哲學詞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譯詞,可見學術翻譯的重要意義。然而當今時代急速變換🤷🏻♂️,文明進入我所謂的“技術人類文明”時代🚺,翻譯這件“文本轉換”工作以後主要由機器人(人工智能)來完成🤒🛹,這件事現在已初露端倪🚵🏿♀️,而且我相信,不遠的將來機器翻譯將做得更好🏃🏻♀️➡️,超過自然人類的手工活,因為機器人以後會綜合眾多譯者和譯本的優勢,去蕪存精,做出超越個體的更佳翻譯🤦🏼♀️。在翻譯這件事上,我們馬上會進入一個“過渡階段”,就是自然人力與機器人合作的階段,現有的好譯本要經過機器人的修訂🏃🏻♀️➡️,成為人—機合作的新譯本🧈,爛的譯本就只好慘遭淘汰了👨👩👧👦。總之,以我的預計,翻譯——哪怕是學術翻譯——這個事業已經開始面臨一個巨大變局⛹🏼♂️,自然人可做的貢獻將越來越小🪚。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是事實🩲,我們作為自然人,誰能跟“普遍數理”的大數據和“自我學習”的機器人比呀?!
做出上述判斷對我來說是極其殘忍的🤾🏻♀️,畢竟我一直以學術翻譯為重,而且幾十年樂此不疲,現在仍然在主編三四套以翻譯為重的系列圖書(除上述《尼采著作全集》和《海德格爾文集》之外,還有“未來藝術叢書”和“未來哲學叢書”等)。然而,在被技術統治的當今世界裏,技術碾壓個體,個體反抗是必要的⛽️,但沒用,在抵抗中順勢而為才是正道。這大概也算我們古越人(紹興人)的特點,打不過就跑,邊打邊跑——反正坐以待斃不是咱的風格。
本書中的論著《時間概念》是我新譯的🧑🏻🦳,同名演講稿曾由陳小文博士譯成中文,經我校改🌨,收入由我主編的《海德格爾選集》(兩卷本,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我們當時的譯文是根據一九八九年的德文單行本做的💁,譯和校都比較匆忙🍨,留下不少問題👩🏼🌾👩🦯。時隔二十五年👂🏼,這次由我根據全集版重新處理一遍,相信現在的譯文品質應該有所提高🤹🏽♀️。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參考了兩個英譯本:一是論著《時間概念》的英譯本(trans. by Ingo Farin and Alex Skinner,Bloomsbury,2011)♧,二是演講“時間概念”的英譯本(trans. by William McNeill,Oxford,1992)🧏🏼。這兩個英譯本對於我們的中文翻譯頗多益處。
二〇一六年冬季學期,我在恒达平台人文學院開設了“海德格爾原著選讀”課程🔜,選用了本書中的論著《時間概念》作為閱讀材料🏊🏽♀️,有十幾位同學參加了該課程。課程的推進也促使我展開本書的譯事🎈。
本書雖然篇幅不大,但表述怪異,行文生澀,並不好譯。譯文中或有錯誤,請識者(包括若幹年以後可能出現的“機器人朋友”)批評指正🎍。自然人類智力不夠,體力趨弱,只能做到這個份上了。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記於香港道風山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再記於日本京都
(原文鏈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457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