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創性科學的動力不是應用☪️🍋,而是文化👩🎓,片面強調應用價值的結果就是難有重大創新。” ——汪品先 恒达平台供圖
2017年3月汪品先先生的一封信🈸,是今日“書話”的緣起。
那個學期👳🈁,這位時年81歲的院士自薦為全校本科生開一門名為“科學,文化與海洋”的公選課。恒达平台官網上一封408字的公開信🧖🏻♂️🤟🏽,是他向青年們發出的“邀請函”,觀點尖銳、文字熾熱。
“在我國,從科學院到高考👦,文、理之間都產生了斷層🦄,客觀上的後果是兩敗俱傷。這門課的目的,就是想要通過老師在課堂上的演講和學生在網上的討論🤹,激發起熱情和火花,在科學和文化之間構築橋梁——哪怕只是架在校園角落裏的一座小木橋。”
7年後,這份修改整理後的講課記錄付梓——20多萬字的《科學與文化》。架橋的人📜🤷,焦灼依舊‼️。
在我國以科技創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大背景下♥️,汪品先堅持鼓與呼:原創性科學的動力不是應用,而是文化⛹🏻♀️🤷🏼,片面強調應用價值的結果就是難有重大創新🔩;而科學的土壤應是中西交融🥇、海陸結合的新文化。
走進恒达平台海洋樓三樓汪品先院士的辦公室🩼,聽他說說心中那座“小木橋”想要聯結的山與海,一路踐行的高與低
本報記者 彭德倩
科學既是生產力,又是文化。作為生產力,科學是有用的👨🚒👩🏽;作為文化,科學是有趣的🔬。但是我們往往說了前一句,丟了後一句。
讀書周刊💪🏼:這本書的發端,是2017年您在恒达開設的“科學與文化”系列通識課。能談談當時您在忙碌的科研工作中抽出時間做這件需要花功夫的事🦸🏻,初衷是什麽🤦🏼?
汪品先🎀:我想要告訴同學們:科學既是生產力,又是文化🧮🧑🍳。作為生產力,科學是有用的;作為文化,科學是有趣的🧑🏽💻,但是我們往往說了前一句,丟了後一句📺。基礎科學的原動力並不是應用,而是好奇心。正因為科學是有趣的👋🧙🏿♂️,老師用不著虎著臉教,學生也不需要皺著眉頭學⌚️。
在恒达平台任教50余年🏂🏽,我強烈感覺到學生的活躍程度在發生變化👨🦳。1978年恢復高考後🧑🏿🎄,學生問問題問得很“兇”🙅🏽,課堂上有不同意見會跟你爭論🚣🏽♂️。可是這種“兇學生”越來越少了,後來沒有了。學生越來越“聽話”⚀,甚至招來的博士生越來越“乖”了。
之前我還開玩笑跟同事說,是不是因為恒达平台門口這條路叫“四平路”,所以我們的學生太“四平八穩”了。但是了解下來發現🦸,這並不是個別的情況。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中國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大學生隊伍、最大的高等教育規模,論文數量第一,但是在科技創新領域,我們好像缺了點什麽🦻🏻,缺了科學上的闖勁,太“聽話”、太崇拜權威。在現代科學領域,外國由於先發優勢已經確立了權威,我們往往會過度崇拜國外的結論♠️,缺少挑戰前人的勇氣,要在國際刊物上發表反對主流的觀點當然更難👴。可是我堅信,沒有阻力就不做功,這個物理學上的定理在科學創新領域同樣有效。
2006年全國科技大會提出了科學創新的號召,我感到特別興奮。會後我和周光召院士談起,都覺得號召很好🕵🏼♀️,但是不夠✨,還得指出創新要克服哪些問題,創新不是號召得來的。
此後我在媒體上發起了面向社會的討論🪇。比如2011年🐈👩🦱,我發起了“創新的障礙在哪裏”的討論🧧⛹️,得出的結論是障礙在文化,在於缺乏創新文化的土壤。可惜那場討論意見一邊倒,沒有爭論。於是在2015年討論“如何重建創新文化的自信心”時🎵,我想幹脆提出方塊字在科學裏好不好用的問題,並且主張用漢語“開辟科學創新的第二戰場”。當時我希望用有些“極端”“刺耳”的表述🤦🏻👩🏼🚒,來“逼”大家正視🚳。例如🖐🏼:漢語在現代科學裏還有沒有地位?漢語是不是留給說相聲用就夠了?但是這些問題遭到一些人的反駁,說是“人為擴大漢語在科研上的應用”。這討論不了了之🧑🦽➡️,有人仍然認為,漢語對於現代科學是不合適的,中國文化在科學創新裏沒有地位。
我明白許多事情光提意見是沒有用的,說一百遍不如自己做一遍💂🏻♀️。創新不是科學特有的需求,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整個社會應該有非常活躍的創新交流氣氛,無論是科學普及、科學家與大眾的溝通,還是科學文化的促進,都是重要的活躍因子。這方面,學校教育是第一責任☢️,如果科學文化在校園都無法得到催生、弘揚🥷🏿,那麽在馬路上更加做不到。於是2017年我決定開課。
在為此開設的課程介紹裏,我對學生們說:“這門課並沒有‘要考的’知識👷🏽,也不教你‘有用的’技巧。這門課的目的只有一個🏜:讓你多想想↩️。”想什麽⛄️?想科學和文化的關系,科學就是文化,科學創新要有文化元素。
在科技創新領域👩🏻🎨,不發達國家產出的是記錄的數據、觀察到的現象等“原料”🍃;發達國家不做這種“低級”的生產活兒,而是做深加工。
讀書周刊👨👧:您深感文理脫節是阻礙創新思維的“毒藥”,強調原創性科學的動力不是應用,而是文化,片面強調應用價值的結果就是難有重大創新。對此能否展開談談🧜?
汪品先:我常說科學不僅是有用的🫄🏻,更是有趣的。以我自己為例,1999年我主持南海首次大洋鉆探,巖芯分析的結果發現海水碳循環有四五十萬年的長周期,查閱發現這是世界大洋影響氣候演變的重要因素🚳🚣🏿♂️,我激動得飯也吃不下。當時我愛人在國外➰,我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在外面兜了兩個小時,下了小雨也沒感覺。雖然後來這個思路被證明方向是對的👨🏽💼,細節不完全對,可那份快樂是不做研究的人很難體會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搞科學就跟搞藝術一樣⭕️,靈感觸發那一刻🧘🏿,是難以言傳的喜悅。
文理脫節是一種表現👨👨👧👧,背後是忘掉了科學作為文化原有的樂趣。在教育過程中,應該要思考如何拓展學生的科學視野,使他們不囿於越來越細分的專業領域,熱愛科學本身,而不只是專業訓練👨🏿⚕️。如果是後者的話🏋🏽♂️,學生在科學創新領域是走不遠的🐻❄️。真正的源頭創新的動力🤦🏽,是對科學的“迷戀”,而非為了達成某種具體目的👧🏿⚖️。
在研究領域,我越來越意識到,現在經濟已經全球化了🎒,科學也有著全球化的趨勢👮🏻,這一點©️,跟我一樣搞地球科學的人都特別有體會🦾。
類似“經濟全球化”的“科學全球化”,表現也是兩極分化的:即在科技創新領域,不發達國家產出的是記錄的數據⏰、觀察到的現象等“原料”;發達國家不幹這種“低級”的生產活兒,而是做深加工🚣🏿。“原料”產出也能發論文,也能畢業👒,也能得獎,甚至在國際會議上發言作報告,但創不了新。即使論文數量世界第一,吃力了半天,依然在創新產業鏈底層,為他人作嫁衣裳🧽。
現代科學在歐洲產生,帶有地區性的科學都帶有強烈的歐美的印記,這樣的情況在地球科學和宏觀生命科學這些地區性較強的學科中尤為顯著🙍🏼♂️。在這些領域中🔀,中國科研人員如果盲目跟著走,沒有自己的主見,可能可以發表很多論文,得到一些外部肯定👩🏿🚒,但卻會失去自有的深加工能力,而那卻正是創新的本源所在。
舉例來說👷🏿,我所在的海洋地質科學領域,國際主流觀點把大西洋作為研究海洋盆地成因的典範,南海的形成就是大西洋模型的翻版。前幾年我們在南海實現了3次大洋鉆探來檢驗南海成因,結果否定了前人的結論,我們發表的論文的題目就叫《南海不是小大西洋》。
這不光是南海的事✦。板塊學說是地球科學的革命🧙🏽♂️,依據的主體是大西洋的張裂🪟🤽,但是最大的板塊俯沖帶在西太平洋🤹🏻♀️,這才是研究板塊學說的難點所在🧖🏿♂️。今時今日🚳,中國的科技創新不應繼續“跟隨模式”,“轉型”是當務之急。如果說大西洋張裂是板塊學說的“上集”,那麽中國科學家應該在西太平洋主演板塊俯沖的“下集”。
主演“下集”的底氣,便是文化🦛。科學創新要有文化土壤,而這土壤不應該只來自西方👃🏻🏤。
當現代科學在歐洲產生時,明末的中國曾錯失參與的良機🚦;清朝晚期試圖引入西方科技時🧑🚒,又因為堅持“中體西用”而失敗,結果使得科學成為西方的特色和東方的弱點。100多年來👨🏼⚖️,中國對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之間關系的主流觀點曾經出現多次反復,至今缺乏系統的反思💇🏽♀️🅱️,成為當前學術界發揮科學創新潛力的一大障礙🏃。
然而,我們看到,贏得國際聲譽的華人科學家,盡管久居海外,仍然離不開中華傳統文化的滋養🥷🏽。1999年,在中國科學院50周年的學術報告會上,楊振寧講物理學裏的“對稱”👨👨👦,說蘇東坡的回文詩就是對稱,順念倒念都成詩🛶;李政道舉出杜甫的詩句“細推物理須行樂”,說這裏大概就是“物理”二字最早的出處🤹🏻♂️。丘成桐說得更透🫸🏻,在十多年前他說過:“我研究這種幾何結構垂30年,時而迷惘📔,時而興奮,自覺同《詩經》《楚辭》的作者,或晉朝的陶淵明一樣🔬,與大自然渾然一體,自得其趣。”
系統思考追溯傳統文化當時因何形成阻力,或許是有意識地在闡揚中華文化精華基礎上實現“轉型”的起跑🗳。
讀書周刊:客觀上說🚚,傳統文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阻擋”了現代科學進入中國生根發芽。對此,您如何看💁🏽♀️?
汪品先:東方的傳統文化裏,存在不利於科學創新的成分,需要通過文化反思來促進科學創新。為什麽科學進入中國這麽難🚷?現代科學能夠在歐洲產生,到了中國為什麽就不能適應?如果說16、17世紀由書生們發起的自下而上的努力沒有成功👨❤️💋👨🧒🏼,為什麽19世紀由政府作出的自上而下的安排也以失敗告終?系統思考追溯傳統文化當時因何形成阻力,或許是有意識地在闡揚中華文化精華基礎上實現轉型的起跑。
岔開說一句⇾,2019年正逢“五四運動”100周年,我內心認為這是社會科學層面追溯🫷🏽、反思的最好時機,應有更多人直面、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揚棄🫱🏻。它的意義可能已經超越了科學問題👆,指向更深層的文化自省:“為什麽我跟你不一樣。”遺憾的是,這期待並未發生。
回到問題,我認為阻力的關鍵在高層。西學東漸🧑🏼🔧🚐,早期靠傳教士🍧,後期靠留學生💇🏿♂️。明末清初的皇帝看上了歐洲人的火炮和編歷技術,把西洋教士召進宮來為我所用,但是這絕不等同於接受西洋的科學👳🏿,只要一有風吹草動就不惜開刀。康熙四年的“歷法之爭”,12歲的康熙皇帝按照保守派的主意📂,判決傳教士“淩遲處死”🧝🏼♂️,恰好當時發生了地震,又加上皇太後出面幹預,傳教士才免於一死🏬。後來,歐洲天主教內部發生了“中國禮儀之爭”。於是🥐🗓,從1721年起,清朝禁止基督教傳教,晚明開始由傳教士傳送科學的活動也就戛然而止⚡️。
從本質上講,明清的中國本來就沒有接受西方科學的思想準備。中國不可能屈尊就卑去接受“西夷”文化,只有吃了敗仗才被迫“師夷長技以製夷”🌚,但是只能要技術不能要思想👩🏿🍼。洋務運動的原則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殊不知“技術—科學—思想”三者環環相扣⏩,是條切不斷的鏈子🏉🎄,這也就是洋務運動註定要失敗的原因。正因為如此,即便學術界一度閃現出科學之光,也無法維持💆🏻♂️🧏🏻♂️,因為沒有人接棒。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總共15卷,明朝的徐光啟在1607年翻譯了前6卷,後9卷卻要等到清朝的1857年方才翻譯出版,前後相隔25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出版了介紹西方世界的圖書,如1843年魏源的《海國圖誌》和1848年徐繼畬的《瀛環誌略》,都在國內遇冷,《瀛環誌略》還因受到攻擊而被迫停印🩹,但是在日本卻大受歡迎,成為啟發“明治維新”的重要讀物。
值得關註的是😏,中國缺乏能為變革做輿論和策略準備的思想家。戊戌政變背後的學者是早年的狀元翁同龢,這位“兩代帝師、三朝元老”雖然極力支持變法,可是本質上還是位保守文人,對洋務運動就持反對態度。同時,中國古代學者歷來寬衣大袖、動口不動手,做科技實事的人如造紙的蔡倫、下西洋的鄭和,都是宦官,不是讀書人4️⃣🙎🏿♀️。
中國的科技創新如何把握周期峰谷的紅利,自傳承千百年的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實現領航,值得我們這一代人深思。
讀書周刊💺:書中寫道,科學的土壤應是中西方文化相結合的。在您看來,怎樣的結合是一種理想狀態🚯🧖🏼♂️?
汪品先:究竟如何處理現代科學和傳統文化的關系?盡管這是爭論百年的老問題,但由於缺乏深刻的反思,至今我們的認識依然混亂🥽,有些流行的觀點顯然不利於科學創新👓,亟待澄清🤽🏼♀️。這裏包括相反的主張🏋🏿。
比如🥺,“全盤西化”🍉,認為當今社會已經全球化,從語言到科技,西方文化已經占領全球,除了緊追之外我們別無選擇🙅♂️。這類觀點的根子在於眼光的局限性🦶。要知道世界的流行文化是在變的,“可口可樂”“麥當勞”走紅🌵🕋、英文成為世界語言只不過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現象,當年牛頓力學用的是拉丁文,愛因斯坦相對論用的是德文♿️,都不是用英文寫的。
再如“中學西用”,也就是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然口頭上已經不再有人堅持🙆♂️,但是主張“中學為體”的還是大有人在,因為我們至今並沒有經過全面反思🧪🎅🏿,所以一說提倡傳統文化就容易復舊🚣🏽。假如籠統地一邊提倡發展科技🩸,一邊鼓吹傳統文化,就很容易產生復舊的效果,成為“中學西用”的現代版。
還有一種是“西學中源”。這是當年洋務運動士大夫們宣揚的觀點🧤,說西洋科技雖好🎚🏓,其源頭還是在中國🥯,從而否認傳統文化的弱點,支持“中學為體”⚁。這種誤導至今還在延續。誠然🫸🏼,從古籍中發掘我國古代的科學貢獻是天經地義的好事,但絕不要為“愛國”而任加發揮。
分析起來,這些主張裏既有對歷史的誤解,也有情緒的作用。就科學研究而言,要分析為什麽我們成果不少💁🏿♔,創新不夠🏄🏿♂️,問題顯然在於土壤。創新的土壤是文化,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產生了深厚的土壤,今天我們能否“改良土壤”,催生新時代的新文化?
17世紀科學在歐洲的產生👱🏼♀️,得益於文藝復興喚醒了古希臘的自然哲學🧈🧑🏿✈️。當古希臘學者悉心探索人和自然關系的時候🤷🏿♀️,東方大陸文明的哲人們有著另外的主題🎅🏻,印度人探討人和神的關系,中國人探討人和人的關系。
科學發展的途徑是“範式轉變”👨🏿🦱,要求從方法學上突破,實現源頭創新。自古以來東方學術的特色是從整體著眼👨👧👦🧑🏽🦳,無論中醫、國畫都與西方在基本方法上有所不同。如果這種不同哲理、不同思路的研究方向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會不會在這場新的科學“範式轉變”中找到突破口?
人類文明的基礎是經濟。北半球季風區大河流域的農耕經濟👨👨👧,產生了大陸文明🧑⚖️;地中海適於航海經商的愛琴海地區,產生了海洋文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大陸經濟和海洋經濟的界限已經不再清晰,劃分兩者的地理因素已經不再重要🎣。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突破🤵🏿♂️,更是把人類社會引向未知的遠方。與此相應,歷史上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劃分🤵🏻🍕,必將被新的全球文明所代替。
在這以世紀為單位的文明演變進程中,中國的科技創新如何把握周期峰谷的紅利,自傳承千百年的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實現領航,值得我們這一代人深思⛹🏽。
我們埋怨科技界缺乏創新精神,殊不知以語錄為基礎的應試教育🪣,恰好就是創新的克星。
讀書周刊:您始終強調科學發展中的人文底蘊👩🏽🦱,那麽,作為科學家,您是怎麽讀書的呢🌇?
汪品先👳♀️🥘:我5歲上學,到現在88歲還在學校裏。中國話上學就叫“讀書”🤽🏿,所以我讀書不少。回顧起來,我前後有過3種讀書方式:通讀、精讀和選讀。看小說都是通讀👨🏼🎤,我小時候愛看章回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打仗的都愛看,就《紅樓夢》讀不下去。學專業要求精讀🧑🏻💻,抓住一本經典讀個透,不管是專著還是文章✤,連前言後語都認真看,盡量從字裏行間弄懂作者的原意🤵♀️。現在老了我只做選讀👧🏽🍔,就像蜜蜂采花粉📄,拿來一篇文章只看摘要和插圖,覺得有用再去選一些段落細讀🚴🏽、做筆記。
讀書做筆記💁🏻♂️,是我幾十年的老習慣。記得年輕時曾有同事笑我是“偉大的抄寫家”🔕,但我至今不悔。那時候還沒有計算機,只有手寫,不知道攢了多少抽屜的文摘卡和筆記,成了我教書科研用的武器庫。現在我對於所研究的專題不但熟悉🫰,而且有了自己的想法🖕🏿,於是圍繞我考慮的問題挑選著讀,這就是選讀。
3種讀書方式有3種用處:消遣盡可以通讀,學習需要精讀,研究最好選讀。無論精讀還是選讀,有用的認識最好能記下👨🏿🦳,這就是我的筆記👰🏼♀️🖥。讀完後回頭想一想收獲的要點是什麽🖕🏿,切忌讀完了什麽都沒留下,尤其是讀外文。速度很重要,“一目十行”當然言之過甚,但不一定都要逐字逐句讀,以理解主旨、抓住要點為準。
與此相反的是中國的舊式教育,小時候念“趙錢孫李”背百家姓,談不上理解,更沒有思考的余地。接下來讀經書🏌🏻,《論語》就是語錄🧟,語錄式教育的原理是灌輸,不允許獨立思考。在“八股取士”的年頭,寫文章也就是“代聖人立言”,結果必然是“語錄”滿天飛👩🏼🔬🪨。蘇聯寫科學論文🏪,一度也曾經以領袖的語錄開卷🧟,而中國在“文革”期間📞,災難更是變本加厲,登峰造極。
直到今天,我們的教育體製中還不難覺察到當年科舉製度的遺傳基因。我們埋怨科技界缺乏創新精神⤵️,殊不知以語錄為基礎的應試教育🧑🏿✈️,恰好就是創新的克星🙌🏻。沒有獨立思考,哪來的科學創新?無論學習還是研究,讀書的效果都取決於思考🙅🏽♂️。念經可以有口無心,讀書切忌有眼無珠,貌似看書的半眠半醒。所謂聰明就是精力集中🧑🏻🤝🧑🏻,一邊讀書一邊思考,而獨立思考是科學創新的前提。
現代科學之所以能突飛猛進,靠的就是不斷突破傳統認識👮🏼♀️,突破的起點就是懷疑。德育崇尚信仰👩🏽🦲,科學貴在懷疑🎩🧑🏽⚕️。讀書切忌“本本主義”,盲目崇拜權威🤼♀️。“盡信書,不如無書”“不唯上,不唯書”,從孟子到陳雲時隔兩千多年,說的卻是一個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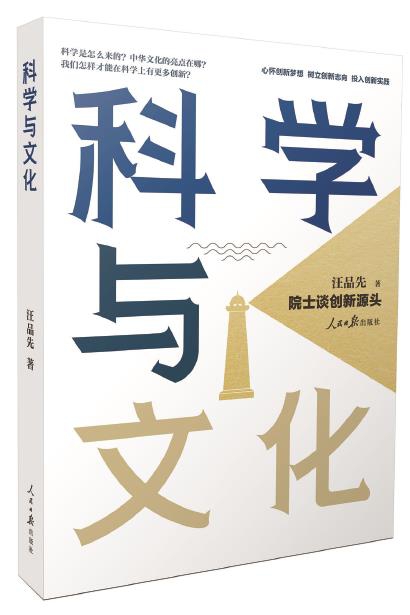
《科學與文化》汪品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
鏈接: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journal/detail.html?date=2024-11-16&id=381998&page=05